在金角湾沿岸的写字楼群拔地而起的很久以前,甚至在清真寺群兴建之前,那里矗立着基督教的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在地平线上独自屹立了一千年。在中世纪,如果人们登上大教堂的屋顶,就能鸟瞰整个“环水之城”,视野极其开阔。站在这里,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君士坦丁堡曾经能够统治世界。
1453年5月29日下午,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就这样登上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屋顶。永载史册的一天终于落幕。就在这一天,他的大军攻克了君士坦丁堡,使得伊斯兰教的预言成为现实,摧毁了拜占庭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最后残余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史官记载道,穆罕默德二世于“真主之灵升上第四层天堂”时登上了大教堂屋顶。
苏丹眼前兵火肆虐、哀鸿遍野。君士坦丁堡遭到了严重破坏和彻底洗劫,“惨遭蹂躏,遍地如同被烈火烤黑一般”。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土崩瓦解,教堂横遭抢劫,末代皇帝也在大屠杀中丧生。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绳索捆成一串,排成长长的队伍,在土耳其人的驱赶下蹒跚行进。空荡荡的房屋上飘荡着旗帜,这表明,屋内的财物已经被洗劫一空。这个春天的傍晚,召唤穆斯林祈祷的呼声徐徐升起,盖过了俘虏们呼天抢地的哀号。这标志着一个皇朝的彻底终结,以及一个新的皇朝凭借征服者的权利正式粉墨登场。土耳其人原先是来自亚洲腹地的游牧部落,此刻在这座欧洲海岸上的城市——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巩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攻克君士坦丁堡的丰功伟绩彻底奠定了穆罕默德二世的地位——他既是拜占庭的继承人,又是伊斯兰圣战无可争议的统帅。
苏丹从他居高望远的有利位置可以追忆土耳其民族的往昔,并憧憬未来。在南面,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南,是安纳托利亚(又称小亚细亚),土耳其人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经过安纳托利亚北上;往北面是欧洲——土耳其人开疆拓土雄心壮志的目标。但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却是西方。在午后的阳光里,马尔马拉海波光粼粼,仿佛锤扁的黄铜。它的西面是广阔的地中海,土耳其人称之为白海。征服了拜占庭之后,穆罕默德继承的不仅仅是一大块土地,更是一个海上帝国。
1453年的事件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个世界之间此消彼长、潮起潮落的斗争的一部分。从11世纪到15世纪,基督教通过十字军东征,曾一度控制了地中海。在希腊海岸地区和爱琴海诸岛上拔地而起的一系列基督教小国家成了十字军东征事业与西方拉丁世界的联系纽带。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他们在巴勒斯坦海岸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阿卡,于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逆转。现在,伊斯兰世界要反击了。
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任何人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雄霸整个地中海,但穆罕默德二世自视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边际。他下定决心,要实现“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他自诩为“两海之王”——白海和黑海。大海对土耳其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大海不是稳定的平地,没有自然边界,没有地方可供游牧民族安营扎寨。人类无法在海上定居。大海并不记得历史:伊斯兰教在此之前曾经在地中海有过立足点,但后来又丢掉了。但穆罕默德二世已经确立了他的宏图大略;在他麾下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是一支庞大的(尽管还缺乏经验)的舰队,而土耳其人非常擅长学习。
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岁月里,穆罕默德二世命人复制了一张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绘制的欧洲地图,并命令希腊人将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他像猎食的猛兽般虎视眈眈地审视着地中海的轮廓布局。他用手指抚摩着地图上的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马赛和巴塞罗那;他追寻着直布罗陀海峡;甚至遥远的不列颠也进入了他的视线。译员们非常谨慎,在地图上把伊斯坦布尔标注得特别突出。穆罕默德二世此时还不知道,在地图的西端,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们正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帝国伟业。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就像两面巨镜,反射着同一轮太阳的光辉;起初它们相距太遥远,互相还不了解。很快,敌意将会使阳光聚焦。托勒密的地图讹误颇多,画着奇形怪状的半岛和歪曲的岛屿,但即便这些错误也无法掩盖关于地中海的这样一个关键事实:它其实是两片海洋,在中间由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狭窄海峡一分为二,马耳他岛就在这海峡的正中间,形成一个尴尬的小点。土耳其人将很快统治地中海东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将总领地中海西部。这两股势力将在马耳他这个点上相遇。
今天,从西班牙南部起飞,横跨整个地中海飞往黎巴嫩海岸,只需三个小时。从空中俯视,地中海一派安静祥和。航船有条不紊、温和驯顺地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行驶。设有城堞的西班牙北岸绵延数千英里,分布有度假村、游艇码头、时髦的度假胜地,以及为南欧经济提供动力的重要港口及工业区。地中海仿佛是一个波澜不兴的礁湖,可以从空中追踪任何一艘船只。古代的可怕风暴曾经摧毁奥德修斯和圣保罗的航船,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船只丝毫不必担心。地中海曾被罗马人称为世界的中心,但在今天我们这个日渐缩小的世界里却显得微不足道。
但在五百年前,地中海给人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海岸地带饥馑遍野,由于农耕和放牧,先是植被遭到破坏,然后土地也变得贫瘠。到14世纪,但丁看到的克里特岛已经是个被生态灾难完全摧毁的地方。“在海中央坐落着一片荒原,”他写道,“它一度是泉水潺潺、树木葱茏的福地,现在却是沙漠。”就连大海也是荒芜的。地中海是由地质结构的猛烈崩溃而形成的,因此从外界进入的清澈海流会猛地跌落到深海沟壑中。地中海也没有像纽芬兰或者北海那样的大陆架可以养育丰饶的鱼群。对于沿海居民来说,这100多万平方英里的海面——它被分割成十几个单独区域,各自有自己独特的气流条件、复杂的海岸和星罗棋布的岛屿——是难以驾驭、硕大无朋和险象环生的。地中海是那么大,以至于东西两个海域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天气良好,一艘帆船从马赛到克里特需要两个月时间;如果天公不作美,就需要六个月。当时船只的适航性惊人的差,风暴往往毫无征兆地骤然降临,海盗多如牛毛,所以水手们往往选择在近海航行,而不敢穿过开阔海域。航海过程中险象环生,登船起航往往就意味着要听天由命。地中海是麻烦重重的海。1453年之后,它将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中心。
欧洲史上最激烈最混乱的斗争之一就在地中海上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争夺世界中心的斗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战火在海上盲目地肆虐了一个多世纪。仅仅是最初的小规模战争——土耳其人借此取代了威尼斯的主导地位——就持续了五十年。这场斗争形式繁多:消耗经济的小规模战争、以信仰的名义进行的海盗突袭、对海岸要塞和港口的袭击、对大型岛屿堡垒的围攻,以及屈指可数的几场史诗级别的大海战。地中海沿岸的所有民族和特殊利益集团都卷入了这场角逐:土耳其人、希腊人、北非人、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和
法国人;亚得里亚海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各民族;商人、帝国捍卫者、海盗和圣战者——他们全都时不时地改旗易辙,为捍卫宗教、贸易或者帝国而战。没有人能够长期保持中立,尽管威尼斯人为此付出了艰难的努力。
这个被陆地环绕的竞技场为冲突对抗提供了无限机遇。地中海在南北方向上惊人地狭窄;在很多地方,只有一衣带水将不同的民族隔开。劫掠者可以突然出现在海平线上,然后又自由自在地离去。自蒙古人的闪电式突袭以来,欧洲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骤然兴起的恐怖入侵。地中海成了一个毫无法度的暴力的生物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无可比拟的残暴互相碰撞。战场就是大海、岛屿和海岸,战局受到风力和天气的影响,主要的武器则是桨帆船。
奥斯曼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基督教世界将他们简单地称为“土耳其人”、“基督之名最残忍的敌人”。在西欧看来,这场斗争是终极战争的来源,是巨大的创伤,也是针对黑暗力量的精神斗争。梵蒂冈内部知道托勒密地图的事情。他们将它想象为奥斯曼帝国征服事业的模板,并以惊人的细节绘声绘色地揣测着高高矗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的托普卡帕宫托普卡帕宫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皇宫,1465~1853年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首都的官邸及主要居所,也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现今则是主要的观光胜地。“托普卡帕”的字面意思是“大炮之门”,昔日城堡内曾放置大炮,由此得名。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9年下令动工兴建托普卡帕宫。内的情景。奥斯曼苏丹戴着典型的土耳其式头巾,身着肥大的土耳其式长袖袍子,长着鹰钩鼻,生性残忍,端坐在富丽堂皇然而透着野蛮劲儿的亭台楼阁内,
研究着通往西方的海道。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消灭基督教。1517年的教皇利奥十世深感土耳其人为心腹大患。“他手中无时无刻不拿着描绘意大利海岸的文件和地图”,教皇心惊胆战地如此描绘苏丹,“他的全副注意力都用于集结火炮、建造船只和勘察欧洲所有的海洋和岛屿。”对土耳其人及其北非盟友来说,对十字军东征报仇雪恨的时机成熟了,扭转世界征服格局和控制贸易的机遇到了。
这场斗争将在宏大的战线上进行,往往远远超越大海的界限。欧洲人在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平原、红海、维也纳城下与敌人激战。但最终,在16世纪,这场斗争的主角们的全副力量都将集中于托勒密地图的中心。这将是一场长达六十年的角逐,由穆罕默德二世的曾孙苏莱曼一世策动。战争于1521年正式爆发,于1565~1571年达到高潮,在这六年的无可比拟的血战中,当时的两个巨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朝将高举各自信仰的战旗,至死方休。这场战争的结局将决定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并影响各帝国在未来的前进方向。
这一切,都从一封信开始。
罗杰·克劳利.jpg)
罗杰·克劳利.jpg)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jpg)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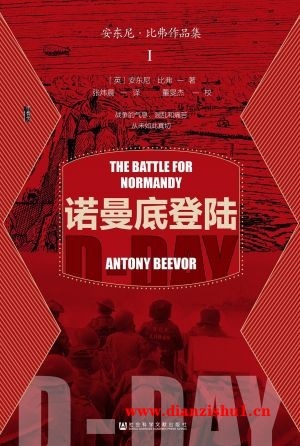
评论留言